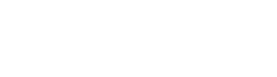【内容提要】
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一书集中概括和论述了道教的生命观和老年观。他提出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口号,强调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把我国古代对生命观和老年观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总结并提炼的“形神兼修”的养生理论和方法,则为我国养生学宝库增添了许多精彩内容。
【关键词】 陶弘景;《养性延命录》;道教老年观
《养性延命录》是我国南北朝时期道教学者陶弘景的一部重要的养生著作。陶弘景(公元456——536年)字通明,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道教思想家、医药学家、炼丹家和文学家,所撰《本草经集注》是中医药史上的经典药物学专著。他的《养性延命录》一书,辑录了自上古至魏晋以来的数十部古籍中的养生学说并加以述评,对道教的养生理论和方法作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尤其是其中提出并论述了“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观念,即要求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达到延年益寿之目的,可说是继承并发展了早期道家和医家的生命观和老年观,为中国传统老年观增添了新的内容并将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细读《养性延命录》一书,其蕴含并体现的道教老年观主要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陶弘景全面继承了早期道家和医家所倡导的道法自然、元气生人、善待生命、修道益寿的老年观思想精华。
按照早期道家的观点,人和天地全都来源于道并统一于道,而且“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人的生命则来源于自然之气的凝聚,所谓“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这个观点与古代医家是一致的,《黄帝内经》说:“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宝命全形论》),而人体的衰老则是自然之气由盛而衰的过程。既然人的生命是自然之气凝聚而成的精华,所以一方面要达观地面对生死,不必要过于贪生怕死,另一方面则要珍视生命,善待生命,“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大宗师》)善待生命最重要的原则和途径是“闻道”、“修道”和“得道”,只有修得了道,才能够益寿并得享天年,甚至达到“与日月参光”、“与天地为常”(《庄子·在宥》)的境界。
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一书,通过详细辑录早期道家道教和医家的养生学说并加以论述和发挥的方式,全面地继承了早期道家和医家的老年观思想精华。据初步统计,全书共辑录了《老子》、《混元道经》、《混元道德经》、《混元妙真经》、《庄子》、《庄子养生篇》、《列子》、《黄老经》、《皇庭经》、《大有经》、《小有经》、《道机经》、《子都经》、《服气经》、《仙经》、《老子指归》、《老君尹氏内解》等近20部早期道家和道教经典,辑录了彭祖、真人、仙人、青牛道士、道士君倩、道人刘京、蒯道人、道林等近10位道教先辈的养生语录,还辑录了《神农经》、《黄帝内经》、《素问》、《元阳经》、《明医论》、《名医叙病论》、《内解》、《导引经》以及岐伯、天老、华佗、吴普、邵仲湛等10多种早期医学经典和著名医家的养生学说。其《养性延命录》序言开首便说:“夫禀气含灵,唯人为贵。人所贵者,盖贵为生。”这里的“禀气含灵唯人为贵”,明显地继承了《庄子》“人之生气之聚也”和《黄帝内经》“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的思想;而“人所贵者盖贵为生”,显然也是从《庄子》的“善吾生者”蜕化演变而来。《序》中又说:此书“或鸠(纠)集仙经真人寿考之规,或得采彭铿老君长龄之术”,“则百年耆寿,是常分也。”明确表示要通过继承早期道家道教和医家的修道养性之术,来达到延命益寿、得享天年的目的。
其次,陶弘景在继承前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口号引入养生理论并加以论证,从而把传统老年观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早在陶弘景之前,晋代的道教学者葛洪已经从他的炼丹实践中提出了“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抱朴子·内篇》)的口号。这个思想,最早来源于他“变化之术何所不为”(同上)的观念。道教历来认为,变化是自然界的一个根本法则。老子说,天地尚不能长久不变,又何况其他东西呢?庄子把天地比喻为一个大熔炉,而万物都在其中经历着熔炼和变化。葛洪说:“变化乃天地之自然”(同上),即把变化看作是宇宙间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他曾借仙人麻姑的口说:“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即已经看到三次沧海变成桑田这样巨大的变化。从小的方面来说各种变化就更多了。以人体为例,甚至会有男人变成女人,女人变成男人这种“男女易形”的情况发生。据此,葛洪又提出“陶冶造化莫灵于人”(同上)的观点,即人可以创造条件去陶冶造化,去改造自然界的事物。例如人可以让马和驴交配而生出骡子,可以用药物来人工制造云雨霜雪,可以通过炼丹把白的铅变成红的丹,再把红的丹还原成白的铅等等。所以他自豪地宣称:“变化之术,何所不为?”人完全有能力去改变事物的性质,创造出符合人类需要的东西来。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一切人间奇迹都是可以创造出来的。葛洪的这一思想,无疑是对早期道家“无为”观念的一个重要突破和发展。道家“无为”的本意虽然并不是绝然消极的无所作为,而是要求人们遵循自然规律,不去强求妄动;但在千变万化的自然界面前,多少带有一点被动和消极的色彩。而葛洪“陶冶造化莫灵于人”一语,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主张人类可以运用“变化之术”去巧夺天工,明显带有一种积极变化的思想,反映了魏晋时期的人们在科学发展基础上不断增强的自信心。
陶弘景继承了葛洪积极变化的思想,进一步把“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口号引入到了人体自身抵抗衰老、延年益寿的养生理论和实践中来。人的体质强弱和寿命长短,究竟是由“天”(自然)所决定的还是由“我”(人)所决定的,这历来是一个问之不得、困惑人类的重大问题。陶弘景引《大有经》中的“疑者”说:同样是一个由阴阳二气凝聚而成的人,同样是生活在天地之间,同样饮食同样呼吸,“而有愚有智,有强有弱,有寿有夭。天耶?人耶?”(《养性延命录·教诫篇第一》)这究竟是“天”(自然)的原因呢还是“人”的原因?接下来他又借“解者”之口引发了一段议论,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论证:
“解者曰:夫形生愚智,天也。强弱寿夭,人也。天道自然,人道自己。始而胎气充实,生而乳食有余,长而滋味不足,壮而声色有节者,强而寿。始而胎气虚耗,生而乳食不足,长而滋味有余,壮而声色自放者,弱而夭。生长全足,加之导养,年未可量。”
这是说,人出生以后的形貌长相以及天资聪敏与否,是由天(自然)来决定的;而他的体质强弱和寿命长短,则是由人来决定的。天道遵循自然,人道则靠自己。如果在怀孕的时候就胎气充实,出生后乳食丰沛,长大后又能少吃那些厚味油腻的东西,壮年时则能够节制声色欲望,那么他一定会强壮而长寿。如果在怀孕的时候就胎气虚耗,出生后乳食不足,长大后又多吃厚味油腻的东西,壮年时则在声色欲望方面自我放纵,那么他一定会体弱而短寿。如果在生长的过程中都非常健全,再加以养性引导,那么他的寿命就不可限量了。所以陶弘景又引《道机》而得出结论说:“人生而命有长短者,非自然也。”(同上)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论证,陶弘景明确提出:“《仙经》曰:我命在我不在天。但愚人不能知此道为生命之要。”(同上)这就是说,他把“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观念视为“生命之要”的“道”,而把不能领悟此道的人们统统视之为“愚人”。这充分体现了陶弘景在养生理论上把道法自然思想与积极变化思想融合起来的创造性风格,从而为道教对生命观和老年观的认识注入了新的内容。这个观点与古代医家在养生保健方面“后天之道,参赞有权,人力居多”(《景岳全书·传忠录》)的思路也是完全一致的,共同为以后的老年养生益寿之道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三,在“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理论指导下,陶弘景倡导“形神兼修”的养生原则,辑录并总结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养生方法。
陶弘景非常赞同汉初道家学者太史公司马谈关于人体形神的认识:“夫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也”(《养性延命录·教诫篇第一》)。这是说,人的生命可以分为“神”(精神)和“形”(形体)两个部分。其中“神”是生命的根本,而“形”则是精神所赖以寄托的具体形象。如果这两方面不能得到很好的保养,“神形早衰,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同上),要想健康长寿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养生的要点,就在于“形神兼修”,同时在“神”和“形”两方面下功夫。在“神”的保养方面,早期道家和道教一直比较重视,其思想核心在于“清静无为”。 例如庄子说:“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乃可以长生。”(《庄子·在宥》)又说:“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惔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庄子·刻意》)陶弘景继承了这一“清静无为”的“养神之道”,在其《养性延命录·序》中明确认为:“若能游心虚静,息虑无为,……则百年耆寿,是常分也。”在《教诫篇第一》中又进一步引严君平《老子指归》说:“游心于虚静,结志于微妙,委虑于无欲,归计于无为,故能达生延命,与道为久。”然而在陶弘景看来,光有“养神之道”还是不够的,还不足以养性延命,还必须配以养“形”之法,方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终极目标。所以他在《养性延命录》一书中辑录了大量的养“形”之法,从而极大地充实和完善了道教的养生学说。
在陶弘景看来,养“形”之法的一个最重要途径,就是“劳形”,也就是要通过运动来锻炼人的形体。他引《列子》的话说:“闲心劳形,养生之方也。”(《养性延命录·教诫篇第一》)这里所说的“闲心”,即是“清静无为”的“养神之道”;所说的“劳形”,即是运动锻炼的养“形”之法。两者兼修,才是完美的“养生之方”。他认为对于人体的保养来说,“劳苦胜于逸乐也”,“夫流水不腐,户枢不朽者,以其劳动数故也。”(同上)流水之所以不腐败,户枢之所以不朽坏,正是因为它们不断运动的缘故。人体也是一样,“养性之道,不欲饱食便卧及终日久坐,皆损寿也。”(《养性延命录·食诫篇第二》)吃饱就睡,整天坐着而不去运动,都是不 利健康并不得长寿的。他特别推崇三国时名医华佗的养生方法。华佗曾对其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人身常摇动,则谷气消,血脉流通,病不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养性延命录·导引按摩篇第五》)这是说,人体要经常运动,但又不能太过分,不能超越它的极限。人身通过经常性的运动,能使吃下去的食物得以消化,血脉得以流通,各种疾病就不容易产生了。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一书中详细辑录了华佗所创制的“五禽戏”,即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来进行运动锻炼的导引术,认为此种锻炼方法能够“消谷气,益气力,除百病”;“能存行之者,必得延年。”(同上)
除了倡导运动养“形”之外,陶弘景在如何对待人的“饮食男女”等日常生活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养生主张。在饮食方面,他主张“食不欲过饱”,“饮不欲过多”;“食欲少而数(多次),不欲顿多难消,常如饱中饥,饥中饱”;“凡食,欲得恒温暖,宜入易消,胜于习冷”;“食毕行数百步,中益也”(以上均见《养生延命录·食诫篇第二》);即倡导饮食不要过度,要恒温忌冷、易于消化、食后百步等等,这些都是符合人体生理要求和医学保健道理的,至今仍有其实用价值。在男女之事方面,陶弘景则主张有所节制而不可纵欲,这对于养生也是有利有益的。
要而言之,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一书集中概括和论述了道教的生命观和老年观。他提出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口号,强调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把我国古代对生命观和老年观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总结并提炼的“形神兼修”的养生理论和方法,则为我国博大精深的养生学宝库增添了许多精彩的内容。
【作者简介】
周瀚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