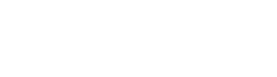吴泽教授上世纪50年代即被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国卷》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历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并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兼召集人;2018年,荣膺首批“上海社科大师”称号。
上世纪80年代,我先后任华东师大历史系、中国史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常去师大一村448号向吴先生请示汇报。那段岁月,先生的家是雾夜里一盏不熄的灯,替初航的我标出第一颗子午星。
先生家陈设简朴,四壁书阵森然,经史子集肃然壁立。二十四史尤为矜重——紫檀匣如古制深衣,匣面鎏金书名,一史一匣,既护卷帙千年之寿,亦存青史一缕精魂。泛黄书页间淡香浮动的,分明是先生与青灯霜雪相对而坐的漫长岁月。
每次我去,他都先笑着叫我坐下,自己却不落座。寒暄间,伸伸手臂,活动筋骨。我原本绷着的那根弦,立马就松了。闲谈时,他尤喜以譬喻阐理,如用“马克思主义走进孔庙”,说明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然而,讲得最多的,还是他亲身经历的往事。那些故事,宛如一部史诗,让我每每屏息。
先生说,我原名吴瑶青,1913年生于常州武进蠡河镇荷花坝村。家贫,少时见佃农终岁劳作,而年终所剩无几,大半收成竟归地主。那些场景深深刺痛了我,心中遂埋下反抗压迫、争取平等的种子。
先生多次说,我2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是祖母和母亲含辛茹苦地将我养大。每说到此处,他声音低下去,像从胸腔深处缓缓托出:母亲每至清明,便在昏黄油灯下剪“挂白”(也称挂五或挂青),将一串串挂白卖得铜钿,换成学费。说到母亲剪挂白,先生喉间一紧,目光破窗而出,似越数十载烟尘,重见那盏油灯下母亲弯如残月的脊背。那种贫困的家庭生活,让先生从小就懂得生活的艰辛,也使他对社会的不公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七岁那年,先生入私塾开蒙。几年后,新式学堂在苏南兴起,他遂走出村塾,先后就读于无锡、常州的小学和中学。1930 年夏,考入大夏大学附属高中部。先生回忆道:“我在上海读高中时,已接触到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等左翼著作,对当时农村土地问题和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有了更深认识。”
1933年9月,先生考入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吕振羽的影响下,他系统研读经典,逐步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1934年撰写了题为《一年来国际经济的回顾与展望》的论文。之后,逐渐转向史学研究,专注于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理论与实证问题,陆续发表了《殷代社会经济研究》《夏代家长制奴隶制经济研究》《中国社会史论战总批判》等论文。
先生追求进步,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翌年,加入由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抗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投身民族救亡的洪流。先生回忆道:“我曾自撰一副春联贴于大门——上联:头颅铸成平等果;下联:铁血爆 发自由花;横批:还我河山。一腔青年血,至今思之犹热。”也正是这一时期,深重的民族灾难促使他确立了“史学研究要为社会现实服务”的信念。
卢沟桥事变后,吴先生从中国大学毕业,随 即回到老家常州,与同学创办《抗敌导报》,激励民众,奋起抗战。然而,因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从沪淞抗战看中日战争的前途》文忤当局,被捕下狱。出狱后再撰《常州沦陷前后与其血底的教训》《发动广泛的民族游击战》等文,锋芒不减。1938年春辗转抵渝,执教于复旦大学、朝阳法学院、大夏大学。为呼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以笔为枪,在史学阵地痛斥帝国主义与法西斯史观,相继发表《中国人种起源论》《中国历史是停滞倒退的么?》等檄文。期间,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历史简编》《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先生曾言:“重庆虽为陪都,仍难逃日机狂轰滥炸。兵荒马乱中,学术研究何其艰难!”空袭警报响起时,众人多携细软奔入防空洞,唯先生背负两袋书籍和书稿,路人皆侧目。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吴泽来到贵州赤水的大夏大学任教,次年随校迁回上海。1946年10月,经翦伯赞、华岗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奉命以地下党员身份坚守讲坛。
内战期间,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校内特务活动猖獗。先生毫无惧色,从未退缩。他利用讲坛宣传进步思想,激励学生反内战。一次上课,他在黑板上写下“梁山何在?”借《水浒》隐喻革命道路。话犹未了,一名三青团学生溜出告密。顷刻,一位进步学生匆匆赶来报信:“吴先生快走,特务来抓您了!”先生趁课间由文史楼侧门从容离去。那一刻,他的勇敢与坚定,以及他对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深深铭刻在学生们心中。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先生参与接收大夏大学,任校务委员、教务长、文学院院长。1951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等校合并为华东师大,先生出任历史系主任。他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对我说:“师资队伍既是学科建设的根基,也是其持续发展的保障。”因此,在先生的努力下,华东师大历史系汇聚了一批史学界的著名教授,如吕思勉、李平心、戴家祥、林举岱、王养冲、陈旭麓、郭圣铭、束世徵、夏冬元等,一时传为佳话。士林遂有“比复旦还强”之说。
八十年代末,我向先生说起要写《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先生拍案称善:“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值得研究。它历史悠久,制度严密,尤其历代遣御史巡察之制,足资今人借鉴。”书稿粗就,先生不辞年高体弱,欣然作序,竟至万言。那篇序言不仅是对我的肯定,更是对我学术生涯的巨大鼓舞。如今,先生虽已驾鹤,而音容宛在。每当我翻检旧书,见那篇万言序,仍觉血脉如潮——那是先生擎与后学的一炬星火,破暗穿岚,长明不灭。
吴泽先生晚年总结一生治学,只寥寥数语:“治史者须‘由今知古’,尤贵‘通古今以指点江山,明未来而经纬天地’。”斯言如炬,至今照人。

- END -
【作者简介】邱永明,男1950年生,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职成所退休教师,长期从事历史学、人才学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出版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